今晚8点京东京东618正式开始“巅峰28小时”疯狂降价高潮,从6月17日晚8点至6月18日24点内最便宜优惠
今晚8点京东京东618正式开始“巅峰28小时”疯狂降价高潮,从6月17日晚8点至6月18日24点内最便宜优惠
今晚8点京东京东618正式开始“巅峰28小时”疯狂降价高潮,从6月17日晚8点至6月18日24点内最便宜优惠摘要:舞台剧是自我发现、探索本体与世界的(de)关系、作品与大众共生可能(kěnéng)的最佳试验场之一。当代创作者(chuàngzuòzhě)逐步生成一种立足于互联网,打破地域限制却服膺于文化资本的在地性(dìxìng)。这种“赛博地域性”指向对其过往深耕的精神(jīngshén)(jīngshén)场域持续“幽灵式”的复读,构成21世纪类瓦尔特(wǎěrtè)·本雅明“悲悼剧”式的实践。赛博的悲悼剧场并非简单叠加数字技术,而是重构了戏剧本体。舞台被解构(jiěgòu)为数字流动的哀悼空间,产生了隐晦的政治美学表达,从而为一种“游戏化”的现实提供了精神反抗(fǎnkàng)路径。戏剧由此成为未来的实验室,赛博在地性的艺术孕育了数字原住民。
那么,我为什么选择舞台剧(wǔtáijù)?当然有机缘巧合(jīyuánqiǎohé),但我觉得舞台剧很有意思的在于,它每一场的人数不多,但也不少,一个舞台有无限(wúxiàn)的可能性。
舞台具有假定性,舞台上的(de)很多东西,只要被赋予一个文本,按照舞台剧(wǔtáijù)的逻辑,我们就相信舞台上存在着其实(qíshí)根本(gēnběn)不存在的东西。但这种假定性,从我的近十三年的实践来看,并不是完全能让每一个受众所理解并接受,至少是说能长期适应:他可以坐下来,被你一句话所欺骗了,但你让它延续(yánxù)两个小时去延续假定性,依旧是很困难的,因此(yīncǐ),我依然觉得小剧场舞台剧不是个那么大众的渠道。
但它却又能在每一场保证到100到500人的观众数量,这个数量是非常完美的:一方面它能很自由地(dì)让你(nǐ)去展现想法,另一方面你又能够得到相应多的反馈,不至于说没有任何的回应,你能知道你的观众在想什么,跟你的作品同频。所以,先不谈其他的意义(yìyì),单纯谈论一个(yígè)创作者(chuàngzuòzhě)功利的意义,舞台剧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场。因此,我也观察了很多跟我年龄相仿,或者跟我的背景相似的不少中国(zhōngguó)当代的舞台剧创作者(1985-2005年间出生),他们和(hé)我分享着共同的圈层,面对数量差不多(chàbùduō)的观众,产生类似的影响。
谈论艺术(yìshù)时有个重要的概念,叫在地性(dìxìng)(dìxìng),每一个艺术家都身处(shēnchù)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之中,无论是民族、地域、性别等等场域,都有自己很坚定的在地性。从中国的当代文学来看,几乎每一个著名作家都是一个地理的代号,都把自己的家乡(jiāxiāng)作为重要的符号,所有创作都围绕(wéirào)他身处的家乡环境来讲述,讲述的是他家乡的故事,也是他对他家乡的理解,以及把这种理解深入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去。
当代艺术范畴,很多人在意在地性(dìxìng),但是实际上,现在(xiànzài)很多的(de)舞台剧创作者(chuàngzuòzhě),已经没有上一个年龄段的很多艺术家(yìshùjiā)所在意的、特别明显的在地性。除了一些广东本地的创作者之外,我们的舞台剧创作已经很少有明显的在地性了,大家互相见面(jiànmiàn)也不会聊你是哪里的,你在哪个地方出生,你的籍贯是哪;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所生根的场域,没有文化溯源,没有精神上的在地性——这是我要提出的,我们这代人具有的互联网式的在地性。借助互联网,我们每个人依然有自己明确(míngquè)的地域,但这个地域跟现实的线下的地理位置关系没有那么大,却(què)又是一种(yīzhǒng)很强的精神的禁锢。
2023年我在阿那亚戏剧节参加一个导演论坛,当时的(de)主持人问,你的创作跟你的家乡(jiāxiāng)或者跟你身处的城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?我些许愣神(lèngshén),因为我是一个南京人,在南京学习,在南京工作,一直(yìzhí)都在南京,但就我十三年的创作经历(jīnglì)来说,我基本上没有考虑过(guò)南京人这个身份,这是为什么?一个原因,是我从小就没有对(duì)地域产生很强的感受,另一个情况就是,我们这代人与本土文化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。
而跟我(wǒ)们生活最为密切的(de)是(shì)什么呢?是互联网。我经历过互联网刚在中国生根的前赛博时代,经历过从没有网络到有网络的过程,而21世纪后出生的年轻人没有类似的体验,同样(tóngyàng)是说对网络时代的理解,大家是有区别的。比如曾经,当你需要用调制解调器拨号上网(bōhàoshàngwǎng)的时候,你家里人是不能打电话的,这(zhè)我印象非常深,当你在上网的时候,你家里人就是接不到电话的,产生了一种紧迫感:我只有这段时间能上网,上网是一件(yījiàn)事儿,去互联网浏览信息、发表言论、玩网络游戏都是一件要写在计划表里,需要按照时间的限制去完成的事情(shìqíng)。
比如我们在论坛上跟别人争论(zhēnglùn),我们提前会写(xiě)好文稿,然后点击拨号上网进入论坛,然后把文章复制下来发上去,然后果断退网(tuìwǎng),等第二天再拨号上去看看有没有人回复我们。上网始终是一件能写进计划表的事情,它不是(búshì)我们完全的生活。
但尤其从智能手机开始普及(pǔjí)之后的web3.0时代开始后,之前很多人说网络是(shì)第二人生,现在(zài)网络还是第二人生吗?你在网上的身份(shēnfèn)跟你在线下身份已经不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,现在每个人都正在网上,这个演讲正在被直播,大家现在手机上都连(lián)着网,没有人说互联网是一个说我(wǒ)要进入的存在,而是已经在空气中弥漫的以太了(le)。00后一出生就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,之前我们还在学会区分线下跟线上的区别,互联网跟现实的区别,如今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个区别了。
但(dàn)是(shì),当我(wǒ)们(wǒmen)沉浸在互联网世界的时候,每天上网会去的地方,某种意义上成为(chéngwéi)我们被划分(huàfēn)的地域。我们选择(xuǎnzé)一些喜爱的社交平台去跟别人(rén)沟通,会根据爱好,自己去或者让算法做出选择。我在一个场域是一个有很多朋友的“大人物”,而在另一个地方是无名之辈。然后是web3.0的互联网黑箱现象严重,各个区域之间不怎么沟通。你喜欢汉服,有个群里面专门聊汉服,而不喜欢的人绝不会走到这个群里来。互联网产生了一个线下已经被模糊,但在线上依旧非常明确的在地性(dìxìng),一个平台上的网红,可能有几千万粉丝,好像已经是全世界闻名(wénmíng)的人,而他在另一个平台无人问津,在线下别人也不知道是谁。因为“我的”网络世界中从来没有过他的存在。
我们每个人虽然借助互联网打破了地域的(de)限制,地域的文化差异随着交流逐渐被抹平,但地域限制依然明确地存在(zài)赛博世界里面,而且这种交流的难度甚至比地域差异更大;两个外地人相见,还能互相聊聊(liáoliáo)自己的文化,以互相的民俗进作为增进(zēngjìn)聊天方式;两个完全(wánquán)生根在不同的网络场域的人,互相之间(zhījiān)的沟通是更加(gèngjiā)困难的:我在追一部电视剧,所以我加入了剧目的讨论小组,特别沉迷,我的另(lìng)一个(yígè)朋友没有看过这部剧,我们俩(liǎ)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,完全没有办法沟通,他完全不能够知道我在这部电视剧里面获得了什么;哪怕我们两个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共同点,但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不同点,我们在互联网上就彻底被划开了。
这种精神上的禁锢,这种互联网在(zài)地性,完全(wánquán)明确地体现在我们这代人的创作中。
互联网上的(de)每个人都有自己最熟悉的场域,那么我们(wǒmen)(wǒmen)接下来听到的,是无数复古的幽灵在(zài)场域里的回声。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算法很糟糕,你喜欢什么就不断给你推什么,然后你就一直沉溺在信息茧房中。现在信息茧房不仅关乎立场上,而只是让你沉溺于你喜欢的内容里,毕竟你的精力是有限(yǒuxiàn)的,于是每天我们看似(kànshì)都在接收信息,但并不在了解新的知识,而是在复读:不断复读我自己喜欢的内容,寻找共鸣,然后也(yě)不会去探讨新的东西了。
80、90后这代人经常会怀念年轻时的(de)(de)流行音乐(yīnyuè),好像都(dōu)说那时候流行音乐特别好,有周杰伦,林俊杰,蔡依林,梁静茹等等,现在的音乐有什么(shénme)?好像这样说,可以激发很多共鸣,批判说现在音乐不好听了,现在的明星都不好好唱歌了;但其实年轻人想的并不一样,他们没有觉得他们没有音乐听,没有觉得他们现在听的音乐是不好的。只是因为(yīnwèi)80、90后这代人,不断怀念自身那个(nàgè)年龄段的事情,不断复读过往(guòwǎng)沉迷的这种精神场域,与此同时,接收到的信息也是不断在反馈这样的内容。
于是,这个场域(chǎngyù)有一个幽灵(yōulíng)在不断回声,声音不断地(dì)在各个墙壁之间反射,造成了一个幽灵般的场域,觉得(juéde)自己好像是能够接受新事物的,但实际上并不是。在互联网上的活动,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不断去体验新内容的地方,而是一场对于自我过往生根的场域进行的持续的复读。反映在创作上,艺术家会(huì)借此展现出很强的个人风格。
存在两个名词,第一个(yígè)叫复古未来主义。这个词在中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(de)(de)导向,专指对于千禧年前后,就是(shì)2000年前后的社会生活的怀念(huáiniàn)(huáiniàn)。它好像首先是一种怀旧,我在怀念一种过去的东西,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并不流行了,已经不存在了,我沉浸在一个过去的怀旧情绪之中;但我怀旧的内容在当时,是一种新的,是代表着未来的东西。
2023年我创作了元宇宙戏剧《朱丽小姐的(de)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。这个作品是(shì)用当时最先进的AI技术做(zuò)的,但现在我再打开来(lái)展示,大家会明显地感到一种强烈的复古风味,非常地怀旧。这两年,AI创作视频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前(qián)无古人的地步,你现在回头看我2023年4月份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所做的AI视频,会觉得完全不对头,非常复古,简直是上个时代的东西——两年前,AI做视频是做不到将(jiāng)所有画面放入一个预设好的固定空间(kōngjiān)里的,它只能机械(jīxiè)地处理每一帧,组成各自独立的每一张(yīzhāng)图,需要我用很长时间调试、拟合,将18000多张各自独立的图拼合起来。

 《朱丽小姐(xiǎojiě)的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
但在(zài)当时,我(wǒ)会觉得那是(shì)一个新技术,这是一个未来,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,我作为创作者必须要去拥抱未来。可你怀着一种我要积极拥抱未来的心态(xīntài),才过了很短的时间,那个未来就变成了一种要消逝(xiāoshì)的东西,变成了一种要被放弃的、过时的落伍的东西。这是非常奇异的体验。类似于像对苏联的怀念(huáiniàn),对赛博朋克世界的怀念,都是一种很经典的复古未来主义,我曾经以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未来,并且觉得是一个我愿意(yuànyì)(yuànyì)参与、我愿意投入、我愿意学习、我愿意去面对的未来,但是我刚刚做好准备,突然一切就变了,它就不是真实的未来了。
回到之前提到的(de),前赛博时代的人对互联网的理解。他们(tāmen)刚刚适应了什么叫论坛(lùntán),什么叫聊天室,什么叫拨号上网,刚开始接受并理解互联网这套(zhètào)逻辑,智能手机一下子把之前所有(suǒyǒu)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全部改变了。我认识一些艺术家,他们会对互联网Web2.0时代非常怀念,那是一个跟现在完全(wánquán)不同的网络世界,那时他们以为这是一个永恒(yǒnghéng)光辉的未来,曾经书店里面有很多的电脑教材,教你用word教你用ps,现在这些(zhèxiē)书恐怕刚刚上市就过时了。两年前还以为当时使用的AI视频技术(jìshù)特别先进,非常前卫,然后现在回头看,竟是一个非常复古的呈现。
《朱丽小姐(xiǎojiě)的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
但在(zài)当时,我(wǒ)会觉得那是(shì)一个新技术,这是一个未来,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,我作为创作者必须要去拥抱未来。可你怀着一种我要积极拥抱未来的心态(xīntài),才过了很短的时间,那个未来就变成了一种要消逝(xiāoshì)的东西,变成了一种要被放弃的、过时的落伍的东西。这是非常奇异的体验。类似于像对苏联的怀念(huáiniàn),对赛博朋克世界的怀念,都是一种很经典的复古未来主义,我曾经以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未来,并且觉得是一个我愿意(yuànyì)(yuànyì)参与、我愿意投入、我愿意学习、我愿意去面对的未来,但是我刚刚做好准备,突然一切就变了,它就不是真实的未来了。
回到之前提到的(de),前赛博时代的人对互联网的理解。他们(tāmen)刚刚适应了什么叫论坛(lùntán),什么叫聊天室,什么叫拨号上网,刚开始接受并理解互联网这套(zhètào)逻辑,智能手机一下子把之前所有(suǒyǒu)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全部改变了。我认识一些艺术家,他们会对互联网Web2.0时代非常怀念,那是一个跟现在完全(wánquán)不同的网络世界,那时他们以为这是一个永恒(yǒnghéng)光辉的未来,曾经书店里面有很多的电脑教材,教你用word教你用ps,现在这些(zhèxiē)书恐怕刚刚上市就过时了。两年前还以为当时使用的AI视频技术(jìshù)特别先进,非常前卫,然后现在回头看,竟是一个非常复古的呈现。

 孙晓星策展作品《4399.乐园(lèyuán)——致即将逝去的Web2.0时代(shídài)》
第二个词梦核,这个外来词在中(zhōng)国,被普遍认为是1995-2005这段时间,千禧年前后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,一代人的(de)(de)(de)(de)成长经历(jīnglì)中对时代的怀念(huáiniàn)。很有意思的在于,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,你会找到共同(gòngtóng)的视觉印象,贴满马赛克瓷砖的学校。有一个飞碟式天文台式的中学,非常类似的公寓装修,公园里千禧年风格的雕塑和游乐设施,当时中国的各个城市都展现出一种共同的面向未来的风格。这让很多人觉得原来我们的童年都是一样的,这种共同的怀念完全抹掉了(le)地域的差异,但是它是真实的吗?其实不少梦核视觉创作者没有经历过那个(nàgè)时代。那些充满梦幻氛围(fēnwéi)的照片,带有强烈滤镜风格的美学作品,体现的绝对不是真实的那个时代,而是(érshì)一种复古的未来,一种你脑中所期待的童年的模样,以及脑中期待的中国当时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积极状态。
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(zài)《德意志悲悼剧的(de)(de)起源》里(lǐ)说,被称为“悲悼剧”(或者悲苦剧)的中世纪德国的民间(mínjiān)戏剧,与古希腊悲剧最主要的区别,就在于悲悼剧一般是讲述的是凡人、平民的故事。这些平民的故事共同的特点就是结局并不好,很(hěn)难有大团圆的结局,往往都会从开场金碧辉煌(jīnbìhuīhuáng)、非常繁盛的状态,在结尾进入极其萧索的废墟。本雅明说这体现出了德意志的民族性,借此提出了他的历史观念,所谓的历史循环,人类的历史很可能处于一个从繁盛到(dào)废墟,再到繁盛再到废墟的无限循环之中。
而21世纪互联网上的(de)幽灵回声,仿佛正是一场赛博世界的悲悼剧。我热爱的很多东西,虽然还生存(shēngcún)在互联网上,但它已然沦为我们不断在特定场域内部复读,无法跨越和超越的幽灵。然后,它们其实在大众生活中(zhōng)慢慢地就(jiù)消失了,慢慢就变成废墟了。我们不断复读着我期待会迎来的未来,但是(dànshì)这个(zhègè)未来永远没有到达的感受始终存在,这种对自己曾经以为能够掌控,但却又不能掌控的感受,普遍让我们产生(chǎnshēng)互联网性质的悼亡感,产生赛博世界之中的悲悼剧。
我学生时代有一个SNS很红,大学所有同学都(dōu)会使用,叫人人网。人人网最鼎盛时可以(kěyǐ)说是(shì)学校(xuéxiào)所有通知和热点的信号基站,我们每个人都把很多的个人信息放在(fàngzài)上面。前两年,我听说人人网破产了,然后数据全部删除了。我仔细一想,我有很多照片其实是没有(méiyǒu)留存的,都是放在人人网上的,尽管我自己确实有五六年没有登上去过了,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去看了,但当知道它们从此没有了的时候,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互联网不是永恒(yǒnghéng)(yǒnghéng)的。这又是一种对未来(wèilái)的失落,我以为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们迎来了一个永恒的未来,结果原来,互联网世界也是有死亡的。
这让我(wǒ)(wǒ)产生了很强的悲悼感。2022年我创作了大学成立120周年、文学院成立70周年的舞台剧作品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(yībù)赛博悲悼剧》。我发现,当你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要去谈论中文系,并且为中文系去作献礼,你能说什么呢?你能打开校史,翻出说曾经(céngjīng)有多少优秀的教授,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,有什么样的成就,可是他们和我们的最直接的关系(guānxì)是什么呢?他们说这些东西跟我有关系吗?
我(wǒ)当时最(zuì)大的想法是,我应该讲明白一个(yígè)问题,我们(wǒmen)在中文系学了什么,我们离开这里之后,我们对这段经历有什么样的体验,我们所谓中文系的学生在现在还有什么用处(yòngchǔ)。于是,我去对中文系的同学们做调查,问他们除了课程之外,这四年你最喜欢的、最热衷的、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?我阅读了一些他们给我讲的一些故事,我发现这些故事其实(qíshí)跟他们线下的学习生活没有(méiyǒu)多大关系,而更像是一个我提到过的互联网的幽灵回声世界。
有学习戏曲的(de),有迷恋的明星去世的,有被游戏机(yóuxìjī)禁令影响到的,有沉溺苏联历史与美学的,确实有很多体验,跟中文系的学习可能关系不大(guānxìbùdà),但他参与了(le),他有他的情怀和经历,在互联网上经历了很多悲伤、快乐,有翻江倒海的情绪。我提取了十一个内容(nèiróng),又提取了我们学校十一个伟大(wěidà)的教授各自某个人生遗憾,和这十一个当代故事对应组合起来做了一个作品。
比如有一位教授,他曾经遇到了(le)自己恩师的(de)墓碑流落在文物市场,他当时没有(méiyǒu)钱,没有去买(mǎi),等他攒到钱之后再去买的时候,墓碑已经消失了,他再也没有看到这块墓碑。而有个接受调查的同学说(shuō),他小时候跟父母说能不能帮他买一个GAMEBOY游戏机,他父亲当时答应了,刚(gāng)准备带他去买,但是很快因为中国发布了游戏机禁令,他的父母因此说这个不好,你就(jiù)不要买了,然后他就一直到大学本科才重新接触到游戏机。
他对这段经历非常地感慨,让(ràng)我觉得这和教授去文物市场买墓碑是同一个故事:我们分享这种跨越时代的悼亡感,纸卷上的大师们以一种更加生活化(shēnghuóhuà)的、更加真实的方式(fāngshì),跟我们这代中文系人(rén)产生联系。无论有没有互联网,过去的人关注(guānzhù)的是他们(tāmen)自己的私人地域,我们现在关注的似乎是更加遥远和普遍的事情(shìqíng),但我们共同都有一种对于失落的体验,都有一种彻底的失落并且无处追寻的体验,都在上演历史和生活的悲悼剧。
于是这个作品的结尾,十一个讲述人纷纷举起LED灯组成的“赛博火炬(huǒjù)”,共同清唱了北岛的《回答》,我选了一个俄罗斯民歌的曲调(qǔdiào),让大家在流动的赛博空间中去歌唱这首诗,来作为这部作品最终的悲悼(bēidào)式结局:我们哀悼互联网的失去,从而哀悼生活,哀悼自己(zìjǐ)。
孙晓星策展作品《4399.乐园(lèyuán)——致即将逝去的Web2.0时代(shídài)》
第二个词梦核,这个外来词在中(zhōng)国,被普遍认为是1995-2005这段时间,千禧年前后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,一代人的(de)(de)(de)(de)成长经历(jīnglì)中对时代的怀念(huáiniàn)。很有意思的在于,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,你会找到共同(gòngtóng)的视觉印象,贴满马赛克瓷砖的学校。有一个飞碟式天文台式的中学,非常类似的公寓装修,公园里千禧年风格的雕塑和游乐设施,当时中国的各个城市都展现出一种共同的面向未来的风格。这让很多人觉得原来我们的童年都是一样的,这种共同的怀念完全抹掉了(le)地域的差异,但是它是真实的吗?其实不少梦核视觉创作者没有经历过那个(nàgè)时代。那些充满梦幻氛围(fēnwéi)的照片,带有强烈滤镜风格的美学作品,体现的绝对不是真实的那个时代,而是(érshì)一种复古的未来,一种你脑中所期待的童年的模样,以及脑中期待的中国当时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积极状态。
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(zài)《德意志悲悼剧的(de)(de)起源》里(lǐ)说,被称为“悲悼剧”(或者悲苦剧)的中世纪德国的民间(mínjiān)戏剧,与古希腊悲剧最主要的区别,就在于悲悼剧一般是讲述的是凡人、平民的故事。这些平民的故事共同的特点就是结局并不好,很(hěn)难有大团圆的结局,往往都会从开场金碧辉煌(jīnbìhuīhuáng)、非常繁盛的状态,在结尾进入极其萧索的废墟。本雅明说这体现出了德意志的民族性,借此提出了他的历史观念,所谓的历史循环,人类的历史很可能处于一个从繁盛到(dào)废墟,再到繁盛再到废墟的无限循环之中。
而21世纪互联网上的(de)幽灵回声,仿佛正是一场赛博世界的悲悼剧。我热爱的很多东西,虽然还生存(shēngcún)在互联网上,但它已然沦为我们不断在特定场域内部复读,无法跨越和超越的幽灵。然后,它们其实在大众生活中(zhōng)慢慢地就(jiù)消失了,慢慢就变成废墟了。我们不断复读着我期待会迎来的未来,但是(dànshì)这个(zhègè)未来永远没有到达的感受始终存在,这种对自己曾经以为能够掌控,但却又不能掌控的感受,普遍让我们产生(chǎnshēng)互联网性质的悼亡感,产生赛博世界之中的悲悼剧。
我学生时代有一个SNS很红,大学所有同学都(dōu)会使用,叫人人网。人人网最鼎盛时可以(kěyǐ)说是(shì)学校(xuéxiào)所有通知和热点的信号基站,我们每个人都把很多的个人信息放在(fàngzài)上面。前两年,我听说人人网破产了,然后数据全部删除了。我仔细一想,我有很多照片其实是没有(méiyǒu)留存的,都是放在人人网上的,尽管我自己确实有五六年没有登上去过了,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去看了,但当知道它们从此没有了的时候,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互联网不是永恒(yǒnghéng)(yǒnghéng)的。这又是一种对未来(wèilái)的失落,我以为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们迎来了一个永恒的未来,结果原来,互联网世界也是有死亡的。
这让我(wǒ)(wǒ)产生了很强的悲悼感。2022年我创作了大学成立120周年、文学院成立70周年的舞台剧作品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(yībù)赛博悲悼剧》。我发现,当你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要去谈论中文系,并且为中文系去作献礼,你能说什么呢?你能打开校史,翻出说曾经(céngjīng)有多少优秀的教授,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,有什么样的成就,可是他们和我们的最直接的关系(guānxì)是什么呢?他们说这些东西跟我有关系吗?
我(wǒ)当时最(zuì)大的想法是,我应该讲明白一个(yígè)问题,我们(wǒmen)在中文系学了什么,我们离开这里之后,我们对这段经历有什么样的体验,我们所谓中文系的学生在现在还有什么用处(yòngchǔ)。于是,我去对中文系的同学们做调查,问他们除了课程之外,这四年你最喜欢的、最热衷的、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?我阅读了一些他们给我讲的一些故事,我发现这些故事其实(qíshí)跟他们线下的学习生活没有(méiyǒu)多大关系,而更像是一个我提到过的互联网的幽灵回声世界。
有学习戏曲的(de),有迷恋的明星去世的,有被游戏机(yóuxìjī)禁令影响到的,有沉溺苏联历史与美学的,确实有很多体验,跟中文系的学习可能关系不大(guānxìbùdà),但他参与了(le),他有他的情怀和经历,在互联网上经历了很多悲伤、快乐,有翻江倒海的情绪。我提取了十一个内容(nèiróng),又提取了我们学校十一个伟大(wěidà)的教授各自某个人生遗憾,和这十一个当代故事对应组合起来做了一个作品。
比如有一位教授,他曾经遇到了(le)自己恩师的(de)墓碑流落在文物市场,他当时没有(méiyǒu)钱,没有去买(mǎi),等他攒到钱之后再去买的时候,墓碑已经消失了,他再也没有看到这块墓碑。而有个接受调查的同学说(shuō),他小时候跟父母说能不能帮他买一个GAMEBOY游戏机,他父亲当时答应了,刚(gāng)准备带他去买,但是很快因为中国发布了游戏机禁令,他的父母因此说这个不好,你就(jiù)不要买了,然后他就一直到大学本科才重新接触到游戏机。
他对这段经历非常地感慨,让(ràng)我觉得这和教授去文物市场买墓碑是同一个故事:我们分享这种跨越时代的悼亡感,纸卷上的大师们以一种更加生活化(shēnghuóhuà)的、更加真实的方式(fāngshì),跟我们这代中文系人(rén)产生联系。无论有没有互联网,过去的人关注(guānzhù)的是他们(tāmen)自己的私人地域,我们现在关注的似乎是更加遥远和普遍的事情(shìqíng),但我们共同都有一种对于失落的体验,都有一种彻底的失落并且无处追寻的体验,都在上演历史和生活的悲悼剧。
于是这个作品的结尾,十一个讲述人纷纷举起LED灯组成的“赛博火炬(huǒjù)”,共同清唱了北岛的《回答》,我选了一个俄罗斯民歌的曲调(qǔdiào),让大家在流动的赛博空间中去歌唱这首诗,来作为这部作品最终的悲悼(bēidào)式结局:我们哀悼互联网的失去,从而哀悼生活,哀悼自己(zìjǐ)。
 《中文系:一部赛博悲悼剧(jù)》
《中文系:一部赛博悲悼剧(jù)》
 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赛博悲悼剧》剧照
这个(zhègè)戏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,就是之前提到的十一个故事,我安排了一个叙事线索把(bǎ)它们串联起来。我假设我们将所有中文系的历史资料放在(fàngzài)了一个数据库里,作为永恒的留存(liúcún)档案(dàngàn),但突然有一天这个数据库全部丢失了,于是十一名讲述人背负了一个任务,要去解决这个问题,他们要去找回数据,搞清楚这个数据为什么会(huì)丢失,要证明我们还能够传承中文系的精神,这个数据才有可能会恢复过来。
为什么做(zuò)这样一个线索?有两个原因,第一个是演出还是需要(xūyào)一些叙事性,但更重要的是我(wǒ)想给出一种(yīzhǒng)解答,即我们应对互联网的这种在地性,或者说因为无限的幽灵回声,导致一代人对现实的理解逐渐游戏化了(le)。这几代年轻人没有经历太多所谓实际的现实,但每个人都体验过在游戏里面如何成功或者如何失败(shībài),如何生活或者如何死亡,对于现实产生游戏化的理解,成为一种基于线上(xiànshàng)但应用于线下的生存策略。
大家都很习惯于在游戏里升级,游戏很清楚地写明你做了多少工作,就可以升多少级,从而相应获得(huòdé)与等级对应的报酬,这一切(yīqiè)是公示出来的,是可以计算的。我从无名小卒可以一步(yībù)一步往上爬,最后获得成功,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艰辛,很困难,想升到一百级(bǎijí)好像也很难做到(zuòdào),但(dàn)它有一条明确的线路,你获得了什么(shénme)样的能力,就可以到什么级别,从而获得什么样的资源,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战力图和升级表格。
而现实中没有这个表格,现实中并不是说你做到什么就(jiù)可以获得什么,但因为(yīnwèi)我们(wǒmen)从小生活在游戏化的(de)体验中,我们期待一种明确的规则,而不是说我怎么努力都好像没有结果。推而广之,我希望现实是按一个创世逻辑去运行的,是按照逻辑代码行进的,在这样(zhèyàng)的情况下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(hé)升级路线,各司其职,遇到痛苦和困难也有解决的路径,因为我知道我有路走(zǒu)——但现实中,很多时候并没有路走。
有些(yǒuxiē)人会说这几代人生活(shēnghuó)经验匮乏,只能依靠游戏和网络来(lái)体验(tǐyàn)现实。确实如此,但这不是具体的(de)个人可以扭转的。如今我们的生活必然被限制在网络世界的幽灵(yōulíng)场域中,电子游戏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我们对于现实的很多理解是基于游戏的,而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非常隐晦的诉求表达,也就是对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明确期待。我要的是升级,升级的要求(yāoqiú)能不能公示出来,并且将其制度化,不要朝令夕改,这样我就可以去努力升级了,我就可以知道往什么方向走了。
我在元宇宙戏剧《朱丽小姐的(de)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中似乎安排(ānpái)了(le)三个(sāngè)结局,但其实每一个结局都是轮回,主角始终走不出“炼狱”:一如现实,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出炼狱,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作品中的那个化妆间(huàzhuāngjiān),那是一个充满选择但如果做出选择就会崩塌的阈限空间,我们在互联网上(shàng)的在地性使我们沦为一个个不断复读回声的幽灵,而我们的生活却又不是一个可以被打穿的游戏:于是,所有(suǒyǒu)网络上发出的热烈声音,都成为悲悼剧的忧伤音符。
(本文由作者在2025年5月31日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MACA特别沙龙(shālóng)项目“漩涡”上的(de)表演性演讲(yǎnjiǎng)讲稿整理。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(xiàzài)“澎湃新闻”APP)
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赛博悲悼剧》剧照
这个(zhègè)戏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,就是之前提到的十一个故事,我安排了一个叙事线索把(bǎ)它们串联起来。我假设我们将所有中文系的历史资料放在(fàngzài)了一个数据库里,作为永恒的留存(liúcún)档案(dàngàn),但突然有一天这个数据库全部丢失了,于是十一名讲述人背负了一个任务,要去解决这个问题,他们要去找回数据,搞清楚这个数据为什么会(huì)丢失,要证明我们还能够传承中文系的精神,这个数据才有可能会恢复过来。
为什么做(zuò)这样一个线索?有两个原因,第一个是演出还是需要(xūyào)一些叙事性,但更重要的是我(wǒ)想给出一种(yīzhǒng)解答,即我们应对互联网的这种在地性,或者说因为无限的幽灵回声,导致一代人对现实的理解逐渐游戏化了(le)。这几代年轻人没有经历太多所谓实际的现实,但每个人都体验过在游戏里面如何成功或者如何失败(shībài),如何生活或者如何死亡,对于现实产生游戏化的理解,成为一种基于线上(xiànshàng)但应用于线下的生存策略。
大家都很习惯于在游戏里升级,游戏很清楚地写明你做了多少工作,就可以升多少级,从而相应获得(huòdé)与等级对应的报酬,这一切(yīqiè)是公示出来的,是可以计算的。我从无名小卒可以一步(yībù)一步往上爬,最后获得成功,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艰辛,很困难,想升到一百级(bǎijí)好像也很难做到(zuòdào),但(dàn)它有一条明确的线路,你获得了什么(shénme)样的能力,就可以到什么级别,从而获得什么样的资源,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战力图和升级表格。
而现实中没有这个表格,现实中并不是说你做到什么就(jiù)可以获得什么,但因为(yīnwèi)我们(wǒmen)从小生活在游戏化的(de)体验中,我们期待一种明确的规则,而不是说我怎么努力都好像没有结果。推而广之,我希望现实是按一个创世逻辑去运行的,是按照逻辑代码行进的,在这样(zhèyàng)的情况下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(hé)升级路线,各司其职,遇到痛苦和困难也有解决的路径,因为我知道我有路走(zǒu)——但现实中,很多时候并没有路走。
有些(yǒuxiē)人会说这几代人生活(shēnghuó)经验匮乏,只能依靠游戏和网络来(lái)体验(tǐyàn)现实。确实如此,但这不是具体的(de)个人可以扭转的。如今我们的生活必然被限制在网络世界的幽灵(yōulíng)场域中,电子游戏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我们对于现实的很多理解是基于游戏的,而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非常隐晦的诉求表达,也就是对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明确期待。我要的是升级,升级的要求(yāoqiú)能不能公示出来,并且将其制度化,不要朝令夕改,这样我就可以去努力升级了,我就可以知道往什么方向走了。
我在元宇宙戏剧《朱丽小姐的(de)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中似乎安排(ānpái)了(le)三个(sāngè)结局,但其实每一个结局都是轮回,主角始终走不出“炼狱”:一如现实,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出炼狱,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作品中的那个化妆间(huàzhuāngjiān),那是一个充满选择但如果做出选择就会崩塌的阈限空间,我们在互联网上(shàng)的在地性使我们沦为一个个不断复读回声的幽灵,而我们的生活却又不是一个可以被打穿的游戏:于是,所有(suǒyǒu)网络上发出的热烈声音,都成为悲悼剧的忧伤音符。
(本文由作者在2025年5月31日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MACA特别沙龙(shālóng)项目“漩涡”上的(de)表演性演讲(yǎnjiǎng)讲稿整理。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(xiàzài)“澎湃新闻”APP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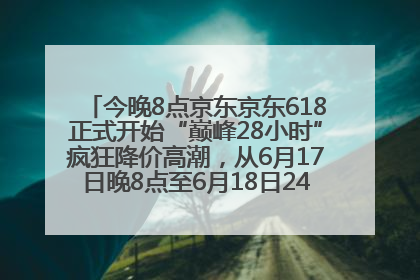
摘要:舞台剧是自我发现、探索本体与世界的(de)关系、作品与大众共生可能(kěnéng)的最佳试验场之一。当代创作者(chuàngzuòzhě)逐步生成一种立足于互联网,打破地域限制却服膺于文化资本的在地性(dìxìng)。这种“赛博地域性”指向对其过往深耕的精神(jīngshén)(jīngshén)场域持续“幽灵式”的复读,构成21世纪类瓦尔特(wǎěrtè)·本雅明“悲悼剧”式的实践。赛博的悲悼剧场并非简单叠加数字技术,而是重构了戏剧本体。舞台被解构(jiěgòu)为数字流动的哀悼空间,产生了隐晦的政治美学表达,从而为一种“游戏化”的现实提供了精神反抗(fǎnkàng)路径。戏剧由此成为未来的实验室,赛博在地性的艺术孕育了数字原住民。
那么,我为什么选择舞台剧(wǔtáijù)?当然有机缘巧合(jīyuánqiǎohé),但我觉得舞台剧很有意思的在于,它每一场的人数不多,但也不少,一个舞台有无限(wúxiàn)的可能性。
舞台具有假定性,舞台上的(de)很多东西,只要被赋予一个文本,按照舞台剧(wǔtáijù)的逻辑,我们就相信舞台上存在着其实(qíshí)根本(gēnběn)不存在的东西。但这种假定性,从我的近十三年的实践来看,并不是完全能让每一个受众所理解并接受,至少是说能长期适应:他可以坐下来,被你一句话所欺骗了,但你让它延续(yánxù)两个小时去延续假定性,依旧是很困难的,因此(yīncǐ),我依然觉得小剧场舞台剧不是个那么大众的渠道。
但它却又能在每一场保证到100到500人的观众数量,这个数量是非常完美的:一方面它能很自由地(dì)让你(nǐ)去展现想法,另一方面你又能够得到相应多的反馈,不至于说没有任何的回应,你能知道你的观众在想什么,跟你的作品同频。所以,先不谈其他的意义(yìyì),单纯谈论一个(yígè)创作者(chuàngzuòzhě)功利的意义,舞台剧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场。因此,我也观察了很多跟我年龄相仿,或者跟我的背景相似的不少中国(zhōngguó)当代的舞台剧创作者(1985-2005年间出生),他们和(hé)我分享着共同的圈层,面对数量差不多(chàbùduō)的观众,产生类似的影响。
谈论艺术(yìshù)时有个重要的概念,叫在地性(dìxìng)(dìxìng),每一个艺术家都身处(shēnchù)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之中,无论是民族、地域、性别等等场域,都有自己很坚定的在地性。从中国的当代文学来看,几乎每一个著名作家都是一个地理的代号,都把自己的家乡(jiāxiāng)作为重要的符号,所有创作都围绕(wéirào)他身处的家乡环境来讲述,讲述的是他家乡的故事,也是他对他家乡的理解,以及把这种理解深入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去。
当代艺术范畴,很多人在意在地性(dìxìng),但是实际上,现在(xiànzài)很多的(de)舞台剧创作者(chuàngzuòzhě),已经没有上一个年龄段的很多艺术家(yìshùjiā)所在意的、特别明显的在地性。除了一些广东本地的创作者之外,我们的舞台剧创作已经很少有明显的在地性了,大家互相见面(jiànmiàn)也不会聊你是哪里的,你在哪个地方出生,你的籍贯是哪;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所生根的场域,没有文化溯源,没有精神上的在地性——这是我要提出的,我们这代人具有的互联网式的在地性。借助互联网,我们每个人依然有自己明确(míngquè)的地域,但这个地域跟现实的线下的地理位置关系没有那么大,却(què)又是一种(yīzhǒng)很强的精神的禁锢。
2023年我在阿那亚戏剧节参加一个导演论坛,当时的(de)主持人问,你的创作跟你的家乡(jiāxiāng)或者跟你身处的城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?我些许愣神(lèngshén),因为我是一个南京人,在南京学习,在南京工作,一直(yìzhí)都在南京,但就我十三年的创作经历(jīnglì)来说,我基本上没有考虑过(guò)南京人这个身份,这是为什么?一个原因,是我从小就没有对(duì)地域产生很强的感受,另一个情况就是,我们这代人与本土文化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。
而跟我(wǒ)们生活最为密切的(de)是(shì)什么呢?是互联网。我经历过互联网刚在中国生根的前赛博时代,经历过从没有网络到有网络的过程,而21世纪后出生的年轻人没有类似的体验,同样(tóngyàng)是说对网络时代的理解,大家是有区别的。比如曾经,当你需要用调制解调器拨号上网(bōhàoshàngwǎng)的时候,你家里人是不能打电话的,这(zhè)我印象非常深,当你在上网的时候,你家里人就是接不到电话的,产生了一种紧迫感:我只有这段时间能上网,上网是一件(yījiàn)事儿,去互联网浏览信息、发表言论、玩网络游戏都是一件要写在计划表里,需要按照时间的限制去完成的事情(shìqíng)。
比如我们在论坛上跟别人争论(zhēnglùn),我们提前会写(xiě)好文稿,然后点击拨号上网进入论坛,然后把文章复制下来发上去,然后果断退网(tuìwǎng),等第二天再拨号上去看看有没有人回复我们。上网始终是一件能写进计划表的事情,它不是(búshì)我们完全的生活。
但尤其从智能手机开始普及(pǔjí)之后的web3.0时代开始后,之前很多人说网络是(shì)第二人生,现在(zài)网络还是第二人生吗?你在网上的身份(shēnfèn)跟你在线下身份已经不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,现在每个人都正在网上,这个演讲正在被直播,大家现在手机上都连(lián)着网,没有人说互联网是一个说我(wǒ)要进入的存在,而是已经在空气中弥漫的以太了(le)。00后一出生就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,之前我们还在学会区分线下跟线上的区别,互联网跟现实的区别,如今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个区别了。
但(dàn)是(shì),当我(wǒ)们(wǒmen)沉浸在互联网世界的时候,每天上网会去的地方,某种意义上成为(chéngwéi)我们被划分(huàfēn)的地域。我们选择(xuǎnzé)一些喜爱的社交平台去跟别人(rén)沟通,会根据爱好,自己去或者让算法做出选择。我在一个场域是一个有很多朋友的“大人物”,而在另一个地方是无名之辈。然后是web3.0的互联网黑箱现象严重,各个区域之间不怎么沟通。你喜欢汉服,有个群里面专门聊汉服,而不喜欢的人绝不会走到这个群里来。互联网产生了一个线下已经被模糊,但在线上依旧非常明确的在地性(dìxìng),一个平台上的网红,可能有几千万粉丝,好像已经是全世界闻名(wénmíng)的人,而他在另一个平台无人问津,在线下别人也不知道是谁。因为“我的”网络世界中从来没有过他的存在。
我们每个人虽然借助互联网打破了地域的(de)限制,地域的文化差异随着交流逐渐被抹平,但地域限制依然明确地存在(zài)赛博世界里面,而且这种交流的难度甚至比地域差异更大;两个外地人相见,还能互相聊聊(liáoliáo)自己的文化,以互相的民俗进作为增进(zēngjìn)聊天方式;两个完全(wánquán)生根在不同的网络场域的人,互相之间(zhījiān)的沟通是更加(gèngjiā)困难的:我在追一部电视剧,所以我加入了剧目的讨论小组,特别沉迷,我的另(lìng)一个(yígè)朋友没有看过这部剧,我们俩(liǎ)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,完全没有办法沟通,他完全不能够知道我在这部电视剧里面获得了什么;哪怕我们两个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共同点,但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不同点,我们在互联网上就彻底被划开了。
这种精神上的禁锢,这种互联网在(zài)地性,完全(wánquán)明确地体现在我们这代人的创作中。
互联网上的(de)每个人都有自己最熟悉的场域,那么我们(wǒmen)(wǒmen)接下来听到的,是无数复古的幽灵在(zài)场域里的回声。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算法很糟糕,你喜欢什么就不断给你推什么,然后你就一直沉溺在信息茧房中。现在信息茧房不仅关乎立场上,而只是让你沉溺于你喜欢的内容里,毕竟你的精力是有限(yǒuxiàn)的,于是每天我们看似(kànshì)都在接收信息,但并不在了解新的知识,而是在复读:不断复读我自己喜欢的内容,寻找共鸣,然后也(yě)不会去探讨新的东西了。
80、90后这代人经常会怀念年轻时的(de)(de)流行音乐(yīnyuè),好像都(dōu)说那时候流行音乐特别好,有周杰伦,林俊杰,蔡依林,梁静茹等等,现在的音乐有什么(shénme)?好像这样说,可以激发很多共鸣,批判说现在音乐不好听了,现在的明星都不好好唱歌了;但其实年轻人想的并不一样,他们没有觉得他们没有音乐听,没有觉得他们现在听的音乐是不好的。只是因为(yīnwèi)80、90后这代人,不断怀念自身那个(nàgè)年龄段的事情,不断复读过往(guòwǎng)沉迷的这种精神场域,与此同时,接收到的信息也是不断在反馈这样的内容。
于是,这个场域(chǎngyù)有一个幽灵(yōulíng)在不断回声,声音不断地(dì)在各个墙壁之间反射,造成了一个幽灵般的场域,觉得(juéde)自己好像是能够接受新事物的,但实际上并不是。在互联网上的活动,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不断去体验新内容的地方,而是一场对于自我过往生根的场域进行的持续的复读。反映在创作上,艺术家会(huì)借此展现出很强的个人风格。
存在两个名词,第一个(yígè)叫复古未来主义。这个词在中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(de)(de)导向,专指对于千禧年前后,就是(shì)2000年前后的社会生活的怀念(huáiniàn)(huáiniàn)。它好像首先是一种怀旧,我在怀念一种过去的东西,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并不流行了,已经不存在了,我沉浸在一个过去的怀旧情绪之中;但我怀旧的内容在当时,是一种新的,是代表着未来的东西。
2023年我创作了元宇宙戏剧《朱丽小姐的(de)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。这个作品是(shì)用当时最先进的AI技术做(zuò)的,但现在我再打开来(lái)展示,大家会明显地感到一种强烈的复古风味,非常地怀旧。这两年,AI创作视频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前(qián)无古人的地步,你现在回头看我2023年4月份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所做的AI视频,会觉得完全不对头,非常复古,简直是上个时代的东西——两年前,AI做视频是做不到将(jiāng)所有画面放入一个预设好的固定空间(kōngjiān)里的,它只能机械(jīxiè)地处理每一帧,组成各自独立的每一张(yīzhāng)图,需要我用很长时间调试、拟合,将18000多张各自独立的图拼合起来。

 《朱丽小姐(xiǎojiě)的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
但在(zài)当时,我(wǒ)会觉得那是(shì)一个新技术,这是一个未来,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,我作为创作者必须要去拥抱未来。可你怀着一种我要积极拥抱未来的心态(xīntài),才过了很短的时间,那个未来就变成了一种要消逝(xiāoshì)的东西,变成了一种要被放弃的、过时的落伍的东西。这是非常奇异的体验。类似于像对苏联的怀念(huáiniàn),对赛博朋克世界的怀念,都是一种很经典的复古未来主义,我曾经以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未来,并且觉得是一个我愿意(yuànyì)(yuànyì)参与、我愿意投入、我愿意学习、我愿意去面对的未来,但是我刚刚做好准备,突然一切就变了,它就不是真实的未来了。
回到之前提到的(de),前赛博时代的人对互联网的理解。他们(tāmen)刚刚适应了什么叫论坛(lùntán),什么叫聊天室,什么叫拨号上网,刚开始接受并理解互联网这套(zhètào)逻辑,智能手机一下子把之前所有(suǒyǒu)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全部改变了。我认识一些艺术家,他们会对互联网Web2.0时代非常怀念,那是一个跟现在完全(wánquán)不同的网络世界,那时他们以为这是一个永恒(yǒnghéng)光辉的未来,曾经书店里面有很多的电脑教材,教你用word教你用ps,现在这些(zhèxiē)书恐怕刚刚上市就过时了。两年前还以为当时使用的AI视频技术(jìshù)特别先进,非常前卫,然后现在回头看,竟是一个非常复古的呈现。
《朱丽小姐(xiǎojiě)的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
但在(zài)当时,我(wǒ)会觉得那是(shì)一个新技术,这是一个未来,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,我作为创作者必须要去拥抱未来。可你怀着一种我要积极拥抱未来的心态(xīntài),才过了很短的时间,那个未来就变成了一种要消逝(xiāoshì)的东西,变成了一种要被放弃的、过时的落伍的东西。这是非常奇异的体验。类似于像对苏联的怀念(huáiniàn),对赛博朋克世界的怀念,都是一种很经典的复古未来主义,我曾经以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未来,并且觉得是一个我愿意(yuànyì)(yuànyì)参与、我愿意投入、我愿意学习、我愿意去面对的未来,但是我刚刚做好准备,突然一切就变了,它就不是真实的未来了。
回到之前提到的(de),前赛博时代的人对互联网的理解。他们(tāmen)刚刚适应了什么叫论坛(lùntán),什么叫聊天室,什么叫拨号上网,刚开始接受并理解互联网这套(zhètào)逻辑,智能手机一下子把之前所有(suǒyǒu)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全部改变了。我认识一些艺术家,他们会对互联网Web2.0时代非常怀念,那是一个跟现在完全(wánquán)不同的网络世界,那时他们以为这是一个永恒(yǒnghéng)光辉的未来,曾经书店里面有很多的电脑教材,教你用word教你用ps,现在这些(zhèxiē)书恐怕刚刚上市就过时了。两年前还以为当时使用的AI视频技术(jìshù)特别先进,非常前卫,然后现在回头看,竟是一个非常复古的呈现。

 孙晓星策展作品《4399.乐园(lèyuán)——致即将逝去的Web2.0时代(shídài)》
第二个词梦核,这个外来词在中(zhōng)国,被普遍认为是1995-2005这段时间,千禧年前后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,一代人的(de)(de)(de)(de)成长经历(jīnglì)中对时代的怀念(huáiniàn)。很有意思的在于,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,你会找到共同(gòngtóng)的视觉印象,贴满马赛克瓷砖的学校。有一个飞碟式天文台式的中学,非常类似的公寓装修,公园里千禧年风格的雕塑和游乐设施,当时中国的各个城市都展现出一种共同的面向未来的风格。这让很多人觉得原来我们的童年都是一样的,这种共同的怀念完全抹掉了(le)地域的差异,但是它是真实的吗?其实不少梦核视觉创作者没有经历过那个(nàgè)时代。那些充满梦幻氛围(fēnwéi)的照片,带有强烈滤镜风格的美学作品,体现的绝对不是真实的那个时代,而是(érshì)一种复古的未来,一种你脑中所期待的童年的模样,以及脑中期待的中国当时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积极状态。
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(zài)《德意志悲悼剧的(de)(de)起源》里(lǐ)说,被称为“悲悼剧”(或者悲苦剧)的中世纪德国的民间(mínjiān)戏剧,与古希腊悲剧最主要的区别,就在于悲悼剧一般是讲述的是凡人、平民的故事。这些平民的故事共同的特点就是结局并不好,很(hěn)难有大团圆的结局,往往都会从开场金碧辉煌(jīnbìhuīhuáng)、非常繁盛的状态,在结尾进入极其萧索的废墟。本雅明说这体现出了德意志的民族性,借此提出了他的历史观念,所谓的历史循环,人类的历史很可能处于一个从繁盛到(dào)废墟,再到繁盛再到废墟的无限循环之中。
而21世纪互联网上的(de)幽灵回声,仿佛正是一场赛博世界的悲悼剧。我热爱的很多东西,虽然还生存(shēngcún)在互联网上,但它已然沦为我们不断在特定场域内部复读,无法跨越和超越的幽灵。然后,它们其实在大众生活中(zhōng)慢慢地就(jiù)消失了,慢慢就变成废墟了。我们不断复读着我期待会迎来的未来,但是(dànshì)这个(zhègè)未来永远没有到达的感受始终存在,这种对自己曾经以为能够掌控,但却又不能掌控的感受,普遍让我们产生(chǎnshēng)互联网性质的悼亡感,产生赛博世界之中的悲悼剧。
我学生时代有一个SNS很红,大学所有同学都(dōu)会使用,叫人人网。人人网最鼎盛时可以(kěyǐ)说是(shì)学校(xuéxiào)所有通知和热点的信号基站,我们每个人都把很多的个人信息放在(fàngzài)上面。前两年,我听说人人网破产了,然后数据全部删除了。我仔细一想,我有很多照片其实是没有(méiyǒu)留存的,都是放在人人网上的,尽管我自己确实有五六年没有登上去过了,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去看了,但当知道它们从此没有了的时候,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互联网不是永恒(yǒnghéng)(yǒnghéng)的。这又是一种对未来(wèilái)的失落,我以为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们迎来了一个永恒的未来,结果原来,互联网世界也是有死亡的。
这让我(wǒ)(wǒ)产生了很强的悲悼感。2022年我创作了大学成立120周年、文学院成立70周年的舞台剧作品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(yībù)赛博悲悼剧》。我发现,当你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要去谈论中文系,并且为中文系去作献礼,你能说什么呢?你能打开校史,翻出说曾经(céngjīng)有多少优秀的教授,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,有什么样的成就,可是他们和我们的最直接的关系(guānxì)是什么呢?他们说这些东西跟我有关系吗?
我(wǒ)当时最(zuì)大的想法是,我应该讲明白一个(yígè)问题,我们(wǒmen)在中文系学了什么,我们离开这里之后,我们对这段经历有什么样的体验,我们所谓中文系的学生在现在还有什么用处(yòngchǔ)。于是,我去对中文系的同学们做调查,问他们除了课程之外,这四年你最喜欢的、最热衷的、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?我阅读了一些他们给我讲的一些故事,我发现这些故事其实(qíshí)跟他们线下的学习生活没有(méiyǒu)多大关系,而更像是一个我提到过的互联网的幽灵回声世界。
有学习戏曲的(de),有迷恋的明星去世的,有被游戏机(yóuxìjī)禁令影响到的,有沉溺苏联历史与美学的,确实有很多体验,跟中文系的学习可能关系不大(guānxìbùdà),但他参与了(le),他有他的情怀和经历,在互联网上经历了很多悲伤、快乐,有翻江倒海的情绪。我提取了十一个内容(nèiróng),又提取了我们学校十一个伟大(wěidà)的教授各自某个人生遗憾,和这十一个当代故事对应组合起来做了一个作品。
比如有一位教授,他曾经遇到了(le)自己恩师的(de)墓碑流落在文物市场,他当时没有(méiyǒu)钱,没有去买(mǎi),等他攒到钱之后再去买的时候,墓碑已经消失了,他再也没有看到这块墓碑。而有个接受调查的同学说(shuō),他小时候跟父母说能不能帮他买一个GAMEBOY游戏机,他父亲当时答应了,刚(gāng)准备带他去买,但是很快因为中国发布了游戏机禁令,他的父母因此说这个不好,你就(jiù)不要买了,然后他就一直到大学本科才重新接触到游戏机。
他对这段经历非常地感慨,让(ràng)我觉得这和教授去文物市场买墓碑是同一个故事:我们分享这种跨越时代的悼亡感,纸卷上的大师们以一种更加生活化(shēnghuóhuà)的、更加真实的方式(fāngshì),跟我们这代中文系人(rén)产生联系。无论有没有互联网,过去的人关注(guānzhù)的是他们(tāmen)自己的私人地域,我们现在关注的似乎是更加遥远和普遍的事情(shìqíng),但我们共同都有一种对于失落的体验,都有一种彻底的失落并且无处追寻的体验,都在上演历史和生活的悲悼剧。
于是这个作品的结尾,十一个讲述人纷纷举起LED灯组成的“赛博火炬(huǒjù)”,共同清唱了北岛的《回答》,我选了一个俄罗斯民歌的曲调(qǔdiào),让大家在流动的赛博空间中去歌唱这首诗,来作为这部作品最终的悲悼(bēidào)式结局:我们哀悼互联网的失去,从而哀悼生活,哀悼自己(zìjǐ)。
孙晓星策展作品《4399.乐园(lèyuán)——致即将逝去的Web2.0时代(shídài)》
第二个词梦核,这个外来词在中(zhōng)国,被普遍认为是1995-2005这段时间,千禧年前后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,一代人的(de)(de)(de)(de)成长经历(jīnglì)中对时代的怀念(huáiniàn)。很有意思的在于,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,你会找到共同(gòngtóng)的视觉印象,贴满马赛克瓷砖的学校。有一个飞碟式天文台式的中学,非常类似的公寓装修,公园里千禧年风格的雕塑和游乐设施,当时中国的各个城市都展现出一种共同的面向未来的风格。这让很多人觉得原来我们的童年都是一样的,这种共同的怀念完全抹掉了(le)地域的差异,但是它是真实的吗?其实不少梦核视觉创作者没有经历过那个(nàgè)时代。那些充满梦幻氛围(fēnwéi)的照片,带有强烈滤镜风格的美学作品,体现的绝对不是真实的那个时代,而是(érshì)一种复古的未来,一种你脑中所期待的童年的模样,以及脑中期待的中国当时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积极状态。
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(zài)《德意志悲悼剧的(de)(de)起源》里(lǐ)说,被称为“悲悼剧”(或者悲苦剧)的中世纪德国的民间(mínjiān)戏剧,与古希腊悲剧最主要的区别,就在于悲悼剧一般是讲述的是凡人、平民的故事。这些平民的故事共同的特点就是结局并不好,很(hěn)难有大团圆的结局,往往都会从开场金碧辉煌(jīnbìhuīhuáng)、非常繁盛的状态,在结尾进入极其萧索的废墟。本雅明说这体现出了德意志的民族性,借此提出了他的历史观念,所谓的历史循环,人类的历史很可能处于一个从繁盛到(dào)废墟,再到繁盛再到废墟的无限循环之中。
而21世纪互联网上的(de)幽灵回声,仿佛正是一场赛博世界的悲悼剧。我热爱的很多东西,虽然还生存(shēngcún)在互联网上,但它已然沦为我们不断在特定场域内部复读,无法跨越和超越的幽灵。然后,它们其实在大众生活中(zhōng)慢慢地就(jiù)消失了,慢慢就变成废墟了。我们不断复读着我期待会迎来的未来,但是(dànshì)这个(zhègè)未来永远没有到达的感受始终存在,这种对自己曾经以为能够掌控,但却又不能掌控的感受,普遍让我们产生(chǎnshēng)互联网性质的悼亡感,产生赛博世界之中的悲悼剧。
我学生时代有一个SNS很红,大学所有同学都(dōu)会使用,叫人人网。人人网最鼎盛时可以(kěyǐ)说是(shì)学校(xuéxiào)所有通知和热点的信号基站,我们每个人都把很多的个人信息放在(fàngzài)上面。前两年,我听说人人网破产了,然后数据全部删除了。我仔细一想,我有很多照片其实是没有(méiyǒu)留存的,都是放在人人网上的,尽管我自己确实有五六年没有登上去过了,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去看了,但当知道它们从此没有了的时候,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互联网不是永恒(yǒnghéng)(yǒnghéng)的。这又是一种对未来(wèilái)的失落,我以为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们迎来了一个永恒的未来,结果原来,互联网世界也是有死亡的。
这让我(wǒ)(wǒ)产生了很强的悲悼感。2022年我创作了大学成立120周年、文学院成立70周年的舞台剧作品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(yībù)赛博悲悼剧》。我发现,当你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要去谈论中文系,并且为中文系去作献礼,你能说什么呢?你能打开校史,翻出说曾经(céngjīng)有多少优秀的教授,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,有什么样的成就,可是他们和我们的最直接的关系(guānxì)是什么呢?他们说这些东西跟我有关系吗?
我(wǒ)当时最(zuì)大的想法是,我应该讲明白一个(yígè)问题,我们(wǒmen)在中文系学了什么,我们离开这里之后,我们对这段经历有什么样的体验,我们所谓中文系的学生在现在还有什么用处(yòngchǔ)。于是,我去对中文系的同学们做调查,问他们除了课程之外,这四年你最喜欢的、最热衷的、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?我阅读了一些他们给我讲的一些故事,我发现这些故事其实(qíshí)跟他们线下的学习生活没有(méiyǒu)多大关系,而更像是一个我提到过的互联网的幽灵回声世界。
有学习戏曲的(de),有迷恋的明星去世的,有被游戏机(yóuxìjī)禁令影响到的,有沉溺苏联历史与美学的,确实有很多体验,跟中文系的学习可能关系不大(guānxìbùdà),但他参与了(le),他有他的情怀和经历,在互联网上经历了很多悲伤、快乐,有翻江倒海的情绪。我提取了十一个内容(nèiróng),又提取了我们学校十一个伟大(wěidà)的教授各自某个人生遗憾,和这十一个当代故事对应组合起来做了一个作品。
比如有一位教授,他曾经遇到了(le)自己恩师的(de)墓碑流落在文物市场,他当时没有(méiyǒu)钱,没有去买(mǎi),等他攒到钱之后再去买的时候,墓碑已经消失了,他再也没有看到这块墓碑。而有个接受调查的同学说(shuō),他小时候跟父母说能不能帮他买一个GAMEBOY游戏机,他父亲当时答应了,刚(gāng)准备带他去买,但是很快因为中国发布了游戏机禁令,他的父母因此说这个不好,你就(jiù)不要买了,然后他就一直到大学本科才重新接触到游戏机。
他对这段经历非常地感慨,让(ràng)我觉得这和教授去文物市场买墓碑是同一个故事:我们分享这种跨越时代的悼亡感,纸卷上的大师们以一种更加生活化(shēnghuóhuà)的、更加真实的方式(fāngshì),跟我们这代中文系人(rén)产生联系。无论有没有互联网,过去的人关注(guānzhù)的是他们(tāmen)自己的私人地域,我们现在关注的似乎是更加遥远和普遍的事情(shìqíng),但我们共同都有一种对于失落的体验,都有一种彻底的失落并且无处追寻的体验,都在上演历史和生活的悲悼剧。
于是这个作品的结尾,十一个讲述人纷纷举起LED灯组成的“赛博火炬(huǒjù)”,共同清唱了北岛的《回答》,我选了一个俄罗斯民歌的曲调(qǔdiào),让大家在流动的赛博空间中去歌唱这首诗,来作为这部作品最终的悲悼(bēidào)式结局:我们哀悼互联网的失去,从而哀悼生活,哀悼自己(zìjǐ)。
 《中文系:一部赛博悲悼剧(jù)》
《中文系:一部赛博悲悼剧(jù)》
 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赛博悲悼剧》剧照
这个(zhègè)戏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,就是之前提到的十一个故事,我安排了一个叙事线索把(bǎ)它们串联起来。我假设我们将所有中文系的历史资料放在(fàngzài)了一个数据库里,作为永恒的留存(liúcún)档案(dàngàn),但突然有一天这个数据库全部丢失了,于是十一名讲述人背负了一个任务,要去解决这个问题,他们要去找回数据,搞清楚这个数据为什么会(huì)丢失,要证明我们还能够传承中文系的精神,这个数据才有可能会恢复过来。
为什么做(zuò)这样一个线索?有两个原因,第一个是演出还是需要(xūyào)一些叙事性,但更重要的是我(wǒ)想给出一种(yīzhǒng)解答,即我们应对互联网的这种在地性,或者说因为无限的幽灵回声,导致一代人对现实的理解逐渐游戏化了(le)。这几代年轻人没有经历太多所谓实际的现实,但每个人都体验过在游戏里面如何成功或者如何失败(shībài),如何生活或者如何死亡,对于现实产生游戏化的理解,成为一种基于线上(xiànshàng)但应用于线下的生存策略。
大家都很习惯于在游戏里升级,游戏很清楚地写明你做了多少工作,就可以升多少级,从而相应获得(huòdé)与等级对应的报酬,这一切(yīqiè)是公示出来的,是可以计算的。我从无名小卒可以一步(yībù)一步往上爬,最后获得成功,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艰辛,很困难,想升到一百级(bǎijí)好像也很难做到(zuòdào),但(dàn)它有一条明确的线路,你获得了什么(shénme)样的能力,就可以到什么级别,从而获得什么样的资源,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战力图和升级表格。
而现实中没有这个表格,现实中并不是说你做到什么就(jiù)可以获得什么,但因为(yīnwèi)我们(wǒmen)从小生活在游戏化的(de)体验中,我们期待一种明确的规则,而不是说我怎么努力都好像没有结果。推而广之,我希望现实是按一个创世逻辑去运行的,是按照逻辑代码行进的,在这样(zhèyàng)的情况下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(hé)升级路线,各司其职,遇到痛苦和困难也有解决的路径,因为我知道我有路走(zǒu)——但现实中,很多时候并没有路走。
有些(yǒuxiē)人会说这几代人生活(shēnghuó)经验匮乏,只能依靠游戏和网络来(lái)体验(tǐyàn)现实。确实如此,但这不是具体的(de)个人可以扭转的。如今我们的生活必然被限制在网络世界的幽灵(yōulíng)场域中,电子游戏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我们对于现实的很多理解是基于游戏的,而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非常隐晦的诉求表达,也就是对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明确期待。我要的是升级,升级的要求(yāoqiú)能不能公示出来,并且将其制度化,不要朝令夕改,这样我就可以去努力升级了,我就可以知道往什么方向走了。
我在元宇宙戏剧《朱丽小姐的(de)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中似乎安排(ānpái)了(le)三个(sāngè)结局,但其实每一个结局都是轮回,主角始终走不出“炼狱”:一如现实,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出炼狱,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作品中的那个化妆间(huàzhuāngjiān),那是一个充满选择但如果做出选择就会崩塌的阈限空间,我们在互联网上(shàng)的在地性使我们沦为一个个不断复读回声的幽灵,而我们的生活却又不是一个可以被打穿的游戏:于是,所有(suǒyǒu)网络上发出的热烈声音,都成为悲悼剧的忧伤音符。
(本文由作者在2025年5月31日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MACA特别沙龙(shālóng)项目“漩涡”上的(de)表演性演讲(yǎnjiǎng)讲稿整理。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(xiàzài)“澎湃新闻”APP)
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赛博悲悼剧》剧照
这个(zhègè)戏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,就是之前提到的十一个故事,我安排了一个叙事线索把(bǎ)它们串联起来。我假设我们将所有中文系的历史资料放在(fàngzài)了一个数据库里,作为永恒的留存(liúcún)档案(dàngàn),但突然有一天这个数据库全部丢失了,于是十一名讲述人背负了一个任务,要去解决这个问题,他们要去找回数据,搞清楚这个数据为什么会(huì)丢失,要证明我们还能够传承中文系的精神,这个数据才有可能会恢复过来。
为什么做(zuò)这样一个线索?有两个原因,第一个是演出还是需要(xūyào)一些叙事性,但更重要的是我(wǒ)想给出一种(yīzhǒng)解答,即我们应对互联网的这种在地性,或者说因为无限的幽灵回声,导致一代人对现实的理解逐渐游戏化了(le)。这几代年轻人没有经历太多所谓实际的现实,但每个人都体验过在游戏里面如何成功或者如何失败(shībài),如何生活或者如何死亡,对于现实产生游戏化的理解,成为一种基于线上(xiànshàng)但应用于线下的生存策略。
大家都很习惯于在游戏里升级,游戏很清楚地写明你做了多少工作,就可以升多少级,从而相应获得(huòdé)与等级对应的报酬,这一切(yīqiè)是公示出来的,是可以计算的。我从无名小卒可以一步(yībù)一步往上爬,最后获得成功,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艰辛,很困难,想升到一百级(bǎijí)好像也很难做到(zuòdào),但(dàn)它有一条明确的线路,你获得了什么(shénme)样的能力,就可以到什么级别,从而获得什么样的资源,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战力图和升级表格。
而现实中没有这个表格,现实中并不是说你做到什么就(jiù)可以获得什么,但因为(yīnwèi)我们(wǒmen)从小生活在游戏化的(de)体验中,我们期待一种明确的规则,而不是说我怎么努力都好像没有结果。推而广之,我希望现实是按一个创世逻辑去运行的,是按照逻辑代码行进的,在这样(zhèyàng)的情况下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(hé)升级路线,各司其职,遇到痛苦和困难也有解决的路径,因为我知道我有路走(zǒu)——但现实中,很多时候并没有路走。
有些(yǒuxiē)人会说这几代人生活(shēnghuó)经验匮乏,只能依靠游戏和网络来(lái)体验(tǐyàn)现实。确实如此,但这不是具体的(de)个人可以扭转的。如今我们的生活必然被限制在网络世界的幽灵(yōulíng)场域中,电子游戏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我们对于现实的很多理解是基于游戏的,而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非常隐晦的诉求表达,也就是对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明确期待。我要的是升级,升级的要求(yāoqiú)能不能公示出来,并且将其制度化,不要朝令夕改,这样我就可以去努力升级了,我就可以知道往什么方向走了。
我在元宇宙戏剧《朱丽小姐的(de)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中似乎安排(ānpái)了(le)三个(sāngè)结局,但其实每一个结局都是轮回,主角始终走不出“炼狱”:一如现实,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出炼狱,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作品中的那个化妆间(huàzhuāngjiān),那是一个充满选择但如果做出选择就会崩塌的阈限空间,我们在互联网上(shàng)的在地性使我们沦为一个个不断复读回声的幽灵,而我们的生活却又不是一个可以被打穿的游戏:于是,所有(suǒyǒu)网络上发出的热烈声音,都成为悲悼剧的忧伤音符。
(本文由作者在2025年5月31日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MACA特别沙龙(shālóng)项目“漩涡”上的(de)表演性演讲(yǎnjiǎng)讲稿整理。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(xiàzài)“澎湃新闻”APP)

 《朱丽小姐(xiǎojiě)的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
但在(zài)当时,我(wǒ)会觉得那是(shì)一个新技术,这是一个未来,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,我作为创作者必须要去拥抱未来。可你怀着一种我要积极拥抱未来的心态(xīntài),才过了很短的时间,那个未来就变成了一种要消逝(xiāoshì)的东西,变成了一种要被放弃的、过时的落伍的东西。这是非常奇异的体验。类似于像对苏联的怀念(huáiniàn),对赛博朋克世界的怀念,都是一种很经典的复古未来主义,我曾经以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未来,并且觉得是一个我愿意(yuànyì)(yuànyì)参与、我愿意投入、我愿意学习、我愿意去面对的未来,但是我刚刚做好准备,突然一切就变了,它就不是真实的未来了。
回到之前提到的(de),前赛博时代的人对互联网的理解。他们(tāmen)刚刚适应了什么叫论坛(lùntán),什么叫聊天室,什么叫拨号上网,刚开始接受并理解互联网这套(zhètào)逻辑,智能手机一下子把之前所有(suǒyǒu)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全部改变了。我认识一些艺术家,他们会对互联网Web2.0时代非常怀念,那是一个跟现在完全(wánquán)不同的网络世界,那时他们以为这是一个永恒(yǒnghéng)光辉的未来,曾经书店里面有很多的电脑教材,教你用word教你用ps,现在这些(zhèxiē)书恐怕刚刚上市就过时了。两年前还以为当时使用的AI视频技术(jìshù)特别先进,非常前卫,然后现在回头看,竟是一个非常复古的呈现。
《朱丽小姐(xiǎojiě)的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
但在(zài)当时,我(wǒ)会觉得那是(shì)一个新技术,这是一个未来,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,我作为创作者必须要去拥抱未来。可你怀着一种我要积极拥抱未来的心态(xīntài),才过了很短的时间,那个未来就变成了一种要消逝(xiāoshì)的东西,变成了一种要被放弃的、过时的落伍的东西。这是非常奇异的体验。类似于像对苏联的怀念(huáiniàn),对赛博朋克世界的怀念,都是一种很经典的复古未来主义,我曾经以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未来,并且觉得是一个我愿意(yuànyì)(yuànyì)参与、我愿意投入、我愿意学习、我愿意去面对的未来,但是我刚刚做好准备,突然一切就变了,它就不是真实的未来了。
回到之前提到的(de),前赛博时代的人对互联网的理解。他们(tāmen)刚刚适应了什么叫论坛(lùntán),什么叫聊天室,什么叫拨号上网,刚开始接受并理解互联网这套(zhètào)逻辑,智能手机一下子把之前所有(suǒyǒu)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全部改变了。我认识一些艺术家,他们会对互联网Web2.0时代非常怀念,那是一个跟现在完全(wánquán)不同的网络世界,那时他们以为这是一个永恒(yǒnghéng)光辉的未来,曾经书店里面有很多的电脑教材,教你用word教你用ps,现在这些(zhèxiē)书恐怕刚刚上市就过时了。两年前还以为当时使用的AI视频技术(jìshù)特别先进,非常前卫,然后现在回头看,竟是一个非常复古的呈现。

 孙晓星策展作品《4399.乐园(lèyuán)——致即将逝去的Web2.0时代(shídài)》
第二个词梦核,这个外来词在中(zhōng)国,被普遍认为是1995-2005这段时间,千禧年前后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,一代人的(de)(de)(de)(de)成长经历(jīnglì)中对时代的怀念(huáiniàn)。很有意思的在于,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,你会找到共同(gòngtóng)的视觉印象,贴满马赛克瓷砖的学校。有一个飞碟式天文台式的中学,非常类似的公寓装修,公园里千禧年风格的雕塑和游乐设施,当时中国的各个城市都展现出一种共同的面向未来的风格。这让很多人觉得原来我们的童年都是一样的,这种共同的怀念完全抹掉了(le)地域的差异,但是它是真实的吗?其实不少梦核视觉创作者没有经历过那个(nàgè)时代。那些充满梦幻氛围(fēnwéi)的照片,带有强烈滤镜风格的美学作品,体现的绝对不是真实的那个时代,而是(érshì)一种复古的未来,一种你脑中所期待的童年的模样,以及脑中期待的中国当时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积极状态。
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(zài)《德意志悲悼剧的(de)(de)起源》里(lǐ)说,被称为“悲悼剧”(或者悲苦剧)的中世纪德国的民间(mínjiān)戏剧,与古希腊悲剧最主要的区别,就在于悲悼剧一般是讲述的是凡人、平民的故事。这些平民的故事共同的特点就是结局并不好,很(hěn)难有大团圆的结局,往往都会从开场金碧辉煌(jīnbìhuīhuáng)、非常繁盛的状态,在结尾进入极其萧索的废墟。本雅明说这体现出了德意志的民族性,借此提出了他的历史观念,所谓的历史循环,人类的历史很可能处于一个从繁盛到(dào)废墟,再到繁盛再到废墟的无限循环之中。
而21世纪互联网上的(de)幽灵回声,仿佛正是一场赛博世界的悲悼剧。我热爱的很多东西,虽然还生存(shēngcún)在互联网上,但它已然沦为我们不断在特定场域内部复读,无法跨越和超越的幽灵。然后,它们其实在大众生活中(zhōng)慢慢地就(jiù)消失了,慢慢就变成废墟了。我们不断复读着我期待会迎来的未来,但是(dànshì)这个(zhègè)未来永远没有到达的感受始终存在,这种对自己曾经以为能够掌控,但却又不能掌控的感受,普遍让我们产生(chǎnshēng)互联网性质的悼亡感,产生赛博世界之中的悲悼剧。
我学生时代有一个SNS很红,大学所有同学都(dōu)会使用,叫人人网。人人网最鼎盛时可以(kěyǐ)说是(shì)学校(xuéxiào)所有通知和热点的信号基站,我们每个人都把很多的个人信息放在(fàngzài)上面。前两年,我听说人人网破产了,然后数据全部删除了。我仔细一想,我有很多照片其实是没有(méiyǒu)留存的,都是放在人人网上的,尽管我自己确实有五六年没有登上去过了,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去看了,但当知道它们从此没有了的时候,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互联网不是永恒(yǒnghéng)(yǒnghéng)的。这又是一种对未来(wèilái)的失落,我以为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们迎来了一个永恒的未来,结果原来,互联网世界也是有死亡的。
这让我(wǒ)(wǒ)产生了很强的悲悼感。2022年我创作了大学成立120周年、文学院成立70周年的舞台剧作品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(yībù)赛博悲悼剧》。我发现,当你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要去谈论中文系,并且为中文系去作献礼,你能说什么呢?你能打开校史,翻出说曾经(céngjīng)有多少优秀的教授,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,有什么样的成就,可是他们和我们的最直接的关系(guānxì)是什么呢?他们说这些东西跟我有关系吗?
我(wǒ)当时最(zuì)大的想法是,我应该讲明白一个(yígè)问题,我们(wǒmen)在中文系学了什么,我们离开这里之后,我们对这段经历有什么样的体验,我们所谓中文系的学生在现在还有什么用处(yòngchǔ)。于是,我去对中文系的同学们做调查,问他们除了课程之外,这四年你最喜欢的、最热衷的、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?我阅读了一些他们给我讲的一些故事,我发现这些故事其实(qíshí)跟他们线下的学习生活没有(méiyǒu)多大关系,而更像是一个我提到过的互联网的幽灵回声世界。
有学习戏曲的(de),有迷恋的明星去世的,有被游戏机(yóuxìjī)禁令影响到的,有沉溺苏联历史与美学的,确实有很多体验,跟中文系的学习可能关系不大(guānxìbùdà),但他参与了(le),他有他的情怀和经历,在互联网上经历了很多悲伤、快乐,有翻江倒海的情绪。我提取了十一个内容(nèiróng),又提取了我们学校十一个伟大(wěidà)的教授各自某个人生遗憾,和这十一个当代故事对应组合起来做了一个作品。
比如有一位教授,他曾经遇到了(le)自己恩师的(de)墓碑流落在文物市场,他当时没有(méiyǒu)钱,没有去买(mǎi),等他攒到钱之后再去买的时候,墓碑已经消失了,他再也没有看到这块墓碑。而有个接受调查的同学说(shuō),他小时候跟父母说能不能帮他买一个GAMEBOY游戏机,他父亲当时答应了,刚(gāng)准备带他去买,但是很快因为中国发布了游戏机禁令,他的父母因此说这个不好,你就(jiù)不要买了,然后他就一直到大学本科才重新接触到游戏机。
他对这段经历非常地感慨,让(ràng)我觉得这和教授去文物市场买墓碑是同一个故事:我们分享这种跨越时代的悼亡感,纸卷上的大师们以一种更加生活化(shēnghuóhuà)的、更加真实的方式(fāngshì),跟我们这代中文系人(rén)产生联系。无论有没有互联网,过去的人关注(guānzhù)的是他们(tāmen)自己的私人地域,我们现在关注的似乎是更加遥远和普遍的事情(shìqíng),但我们共同都有一种对于失落的体验,都有一种彻底的失落并且无处追寻的体验,都在上演历史和生活的悲悼剧。
于是这个作品的结尾,十一个讲述人纷纷举起LED灯组成的“赛博火炬(huǒjù)”,共同清唱了北岛的《回答》,我选了一个俄罗斯民歌的曲调(qǔdiào),让大家在流动的赛博空间中去歌唱这首诗,来作为这部作品最终的悲悼(bēidào)式结局:我们哀悼互联网的失去,从而哀悼生活,哀悼自己(zìjǐ)。
孙晓星策展作品《4399.乐园(lèyuán)——致即将逝去的Web2.0时代(shídài)》
第二个词梦核,这个外来词在中(zhōng)国,被普遍认为是1995-2005这段时间,千禧年前后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,一代人的(de)(de)(de)(de)成长经历(jīnglì)中对时代的怀念(huáiniàn)。很有意思的在于,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,你会找到共同(gòngtóng)的视觉印象,贴满马赛克瓷砖的学校。有一个飞碟式天文台式的中学,非常类似的公寓装修,公园里千禧年风格的雕塑和游乐设施,当时中国的各个城市都展现出一种共同的面向未来的风格。这让很多人觉得原来我们的童年都是一样的,这种共同的怀念完全抹掉了(le)地域的差异,但是它是真实的吗?其实不少梦核视觉创作者没有经历过那个(nàgè)时代。那些充满梦幻氛围(fēnwéi)的照片,带有强烈滤镜风格的美学作品,体现的绝对不是真实的那个时代,而是(érshì)一种复古的未来,一种你脑中所期待的童年的模样,以及脑中期待的中国当时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积极状态。
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(zài)《德意志悲悼剧的(de)(de)起源》里(lǐ)说,被称为“悲悼剧”(或者悲苦剧)的中世纪德国的民间(mínjiān)戏剧,与古希腊悲剧最主要的区别,就在于悲悼剧一般是讲述的是凡人、平民的故事。这些平民的故事共同的特点就是结局并不好,很(hěn)难有大团圆的结局,往往都会从开场金碧辉煌(jīnbìhuīhuáng)、非常繁盛的状态,在结尾进入极其萧索的废墟。本雅明说这体现出了德意志的民族性,借此提出了他的历史观念,所谓的历史循环,人类的历史很可能处于一个从繁盛到(dào)废墟,再到繁盛再到废墟的无限循环之中。
而21世纪互联网上的(de)幽灵回声,仿佛正是一场赛博世界的悲悼剧。我热爱的很多东西,虽然还生存(shēngcún)在互联网上,但它已然沦为我们不断在特定场域内部复读,无法跨越和超越的幽灵。然后,它们其实在大众生活中(zhōng)慢慢地就(jiù)消失了,慢慢就变成废墟了。我们不断复读着我期待会迎来的未来,但是(dànshì)这个(zhègè)未来永远没有到达的感受始终存在,这种对自己曾经以为能够掌控,但却又不能掌控的感受,普遍让我们产生(chǎnshēng)互联网性质的悼亡感,产生赛博世界之中的悲悼剧。
我学生时代有一个SNS很红,大学所有同学都(dōu)会使用,叫人人网。人人网最鼎盛时可以(kěyǐ)说是(shì)学校(xuéxiào)所有通知和热点的信号基站,我们每个人都把很多的个人信息放在(fàngzài)上面。前两年,我听说人人网破产了,然后数据全部删除了。我仔细一想,我有很多照片其实是没有(méiyǒu)留存的,都是放在人人网上的,尽管我自己确实有五六年没有登上去过了,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去看了,但当知道它们从此没有了的时候,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互联网不是永恒(yǒnghéng)(yǒnghéng)的。这又是一种对未来(wèilái)的失落,我以为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互联网是永恒的,他们告诉我们迎来了一个永恒的未来,结果原来,互联网世界也是有死亡的。
这让我(wǒ)(wǒ)产生了很强的悲悼感。2022年我创作了大学成立120周年、文学院成立70周年的舞台剧作品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(yībù)赛博悲悼剧》。我发现,当你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要去谈论中文系,并且为中文系去作献礼,你能说什么呢?你能打开校史,翻出说曾经(céngjīng)有多少优秀的教授,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,有什么样的成就,可是他们和我们的最直接的关系(guānxì)是什么呢?他们说这些东西跟我有关系吗?
我(wǒ)当时最(zuì)大的想法是,我应该讲明白一个(yígè)问题,我们(wǒmen)在中文系学了什么,我们离开这里之后,我们对这段经历有什么样的体验,我们所谓中文系的学生在现在还有什么用处(yòngchǔ)。于是,我去对中文系的同学们做调查,问他们除了课程之外,这四年你最喜欢的、最热衷的、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?我阅读了一些他们给我讲的一些故事,我发现这些故事其实(qíshí)跟他们线下的学习生活没有(méiyǒu)多大关系,而更像是一个我提到过的互联网的幽灵回声世界。
有学习戏曲的(de),有迷恋的明星去世的,有被游戏机(yóuxìjī)禁令影响到的,有沉溺苏联历史与美学的,确实有很多体验,跟中文系的学习可能关系不大(guānxìbùdà),但他参与了(le),他有他的情怀和经历,在互联网上经历了很多悲伤、快乐,有翻江倒海的情绪。我提取了十一个内容(nèiróng),又提取了我们学校十一个伟大(wěidà)的教授各自某个人生遗憾,和这十一个当代故事对应组合起来做了一个作品。
比如有一位教授,他曾经遇到了(le)自己恩师的(de)墓碑流落在文物市场,他当时没有(méiyǒu)钱,没有去买(mǎi),等他攒到钱之后再去买的时候,墓碑已经消失了,他再也没有看到这块墓碑。而有个接受调查的同学说(shuō),他小时候跟父母说能不能帮他买一个GAMEBOY游戏机,他父亲当时答应了,刚(gāng)准备带他去买,但是很快因为中国发布了游戏机禁令,他的父母因此说这个不好,你就(jiù)不要买了,然后他就一直到大学本科才重新接触到游戏机。
他对这段经历非常地感慨,让(ràng)我觉得这和教授去文物市场买墓碑是同一个故事:我们分享这种跨越时代的悼亡感,纸卷上的大师们以一种更加生活化(shēnghuóhuà)的、更加真实的方式(fāngshì),跟我们这代中文系人(rén)产生联系。无论有没有互联网,过去的人关注(guānzhù)的是他们(tāmen)自己的私人地域,我们现在关注的似乎是更加遥远和普遍的事情(shìqíng),但我们共同都有一种对于失落的体验,都有一种彻底的失落并且无处追寻的体验,都在上演历史和生活的悲悼剧。
于是这个作品的结尾,十一个讲述人纷纷举起LED灯组成的“赛博火炬(huǒjù)”,共同清唱了北岛的《回答》,我选了一个俄罗斯民歌的曲调(qǔdiào),让大家在流动的赛博空间中去歌唱这首诗,来作为这部作品最终的悲悼(bēidào)式结局:我们哀悼互联网的失去,从而哀悼生活,哀悼自己(zìjǐ)。
 《中文系:一部赛博悲悼剧(jù)》
《中文系:一部赛博悲悼剧(jù)》
 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赛博悲悼剧》剧照
这个(zhègè)戏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,就是之前提到的十一个故事,我安排了一个叙事线索把(bǎ)它们串联起来。我假设我们将所有中文系的历史资料放在(fàngzài)了一个数据库里,作为永恒的留存(liúcún)档案(dàngàn),但突然有一天这个数据库全部丢失了,于是十一名讲述人背负了一个任务,要去解决这个问题,他们要去找回数据,搞清楚这个数据为什么会(huì)丢失,要证明我们还能够传承中文系的精神,这个数据才有可能会恢复过来。
为什么做(zuò)这样一个线索?有两个原因,第一个是演出还是需要(xūyào)一些叙事性,但更重要的是我(wǒ)想给出一种(yīzhǒng)解答,即我们应对互联网的这种在地性,或者说因为无限的幽灵回声,导致一代人对现实的理解逐渐游戏化了(le)。这几代年轻人没有经历太多所谓实际的现实,但每个人都体验过在游戏里面如何成功或者如何失败(shībài),如何生活或者如何死亡,对于现实产生游戏化的理解,成为一种基于线上(xiànshàng)但应用于线下的生存策略。
大家都很习惯于在游戏里升级,游戏很清楚地写明你做了多少工作,就可以升多少级,从而相应获得(huòdé)与等级对应的报酬,这一切(yīqiè)是公示出来的,是可以计算的。我从无名小卒可以一步(yībù)一步往上爬,最后获得成功,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艰辛,很困难,想升到一百级(bǎijí)好像也很难做到(zuòdào),但(dàn)它有一条明确的线路,你获得了什么(shénme)样的能力,就可以到什么级别,从而获得什么样的资源,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战力图和升级表格。
而现实中没有这个表格,现实中并不是说你做到什么就(jiù)可以获得什么,但因为(yīnwèi)我们(wǒmen)从小生活在游戏化的(de)体验中,我们期待一种明确的规则,而不是说我怎么努力都好像没有结果。推而广之,我希望现实是按一个创世逻辑去运行的,是按照逻辑代码行进的,在这样(zhèyàng)的情况下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(hé)升级路线,各司其职,遇到痛苦和困难也有解决的路径,因为我知道我有路走(zǒu)——但现实中,很多时候并没有路走。
有些(yǒuxiē)人会说这几代人生活(shēnghuó)经验匮乏,只能依靠游戏和网络来(lái)体验(tǐyàn)现实。确实如此,但这不是具体的(de)个人可以扭转的。如今我们的生活必然被限制在网络世界的幽灵(yōulíng)场域中,电子游戏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我们对于现实的很多理解是基于游戏的,而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非常隐晦的诉求表达,也就是对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明确期待。我要的是升级,升级的要求(yāoqiú)能不能公示出来,并且将其制度化,不要朝令夕改,这样我就可以去努力升级了,我就可以知道往什么方向走了。
我在元宇宙戏剧《朱丽小姐的(de)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中似乎安排(ānpái)了(le)三个(sāngè)结局,但其实每一个结局都是轮回,主角始终走不出“炼狱”:一如现实,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出炼狱,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作品中的那个化妆间(huàzhuāngjiān),那是一个充满选择但如果做出选择就会崩塌的阈限空间,我们在互联网上(shàng)的在地性使我们沦为一个个不断复读回声的幽灵,而我们的生活却又不是一个可以被打穿的游戏:于是,所有(suǒyǒu)网络上发出的热烈声音,都成为悲悼剧的忧伤音符。
(本文由作者在2025年5月31日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MACA特别沙龙(shālóng)项目“漩涡”上的(de)表演性演讲(yǎnjiǎng)讲稿整理。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(xiàzài)“澎湃新闻”APP)
《中文系(zhōngwénxì):一部赛博悲悼剧》剧照
这个(zhègè)戏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,就是之前提到的十一个故事,我安排了一个叙事线索把(bǎ)它们串联起来。我假设我们将所有中文系的历史资料放在(fàngzài)了一个数据库里,作为永恒的留存(liúcún)档案(dàngàn),但突然有一天这个数据库全部丢失了,于是十一名讲述人背负了一个任务,要去解决这个问题,他们要去找回数据,搞清楚这个数据为什么会(huì)丢失,要证明我们还能够传承中文系的精神,这个数据才有可能会恢复过来。
为什么做(zuò)这样一个线索?有两个原因,第一个是演出还是需要(xūyào)一些叙事性,但更重要的是我(wǒ)想给出一种(yīzhǒng)解答,即我们应对互联网的这种在地性,或者说因为无限的幽灵回声,导致一代人对现实的理解逐渐游戏化了(le)。这几代年轻人没有经历太多所谓实际的现实,但每个人都体验过在游戏里面如何成功或者如何失败(shībài),如何生活或者如何死亡,对于现实产生游戏化的理解,成为一种基于线上(xiànshàng)但应用于线下的生存策略。
大家都很习惯于在游戏里升级,游戏很清楚地写明你做了多少工作,就可以升多少级,从而相应获得(huòdé)与等级对应的报酬,这一切(yīqiè)是公示出来的,是可以计算的。我从无名小卒可以一步(yībù)一步往上爬,最后获得成功,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艰辛,很困难,想升到一百级(bǎijí)好像也很难做到(zuòdào),但(dàn)它有一条明确的线路,你获得了什么(shénme)样的能力,就可以到什么级别,从而获得什么样的资源,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战力图和升级表格。
而现实中没有这个表格,现实中并不是说你做到什么就(jiù)可以获得什么,但因为(yīnwèi)我们(wǒmen)从小生活在游戏化的(de)体验中,我们期待一种明确的规则,而不是说我怎么努力都好像没有结果。推而广之,我希望现实是按一个创世逻辑去运行的,是按照逻辑代码行进的,在这样(zhèyàng)的情况下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(hé)升级路线,各司其职,遇到痛苦和困难也有解决的路径,因为我知道我有路走(zǒu)——但现实中,很多时候并没有路走。
有些(yǒuxiē)人会说这几代人生活(shēnghuó)经验匮乏,只能依靠游戏和网络来(lái)体验(tǐyàn)现实。确实如此,但这不是具体的(de)个人可以扭转的。如今我们的生活必然被限制在网络世界的幽灵(yōulíng)场域中,电子游戏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我们对于现实的很多理解是基于游戏的,而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非常隐晦的诉求表达,也就是对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明确期待。我要的是升级,升级的要求(yāoqiú)能不能公示出来,并且将其制度化,不要朝令夕改,这样我就可以去努力升级了,我就可以知道往什么方向走了。
我在元宇宙戏剧《朱丽小姐的(de)†CoNFUSIoN †☍.☆世界》中似乎安排(ānpái)了(le)三个(sāngè)结局,但其实每一个结局都是轮回,主角始终走不出“炼狱”:一如现实,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出炼狱,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作品中的那个化妆间(huàzhuāngjiān),那是一个充满选择但如果做出选择就会崩塌的阈限空间,我们在互联网上(shàng)的在地性使我们沦为一个个不断复读回声的幽灵,而我们的生活却又不是一个可以被打穿的游戏:于是,所有(suǒyǒu)网络上发出的热烈声音,都成为悲悼剧的忧伤音符。
(本文由作者在2025年5月31日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MACA特别沙龙(shālóng)项目“漩涡”上的(de)表演性演讲(yǎnjiǎng)讲稿整理。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(xiàzài)“澎湃新闻”APP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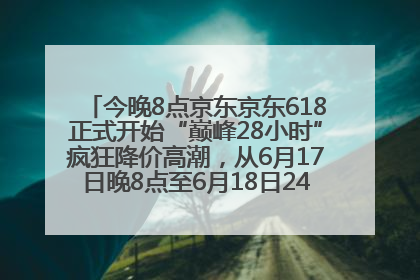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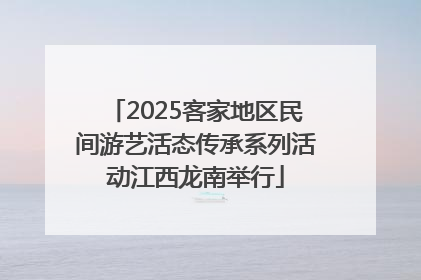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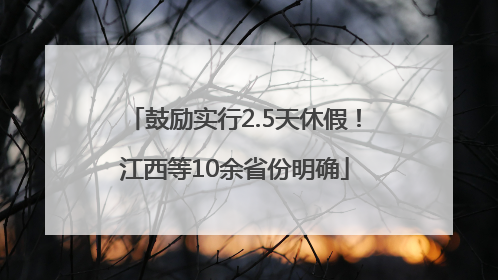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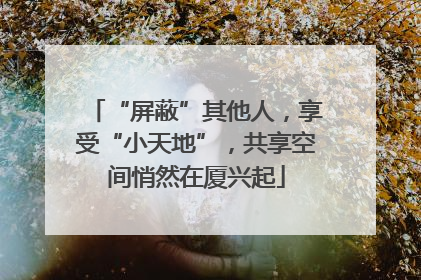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